|
云点软件 http://yundianruanjian.com 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无疑是当代最受瞩目的美国汉学家之一,他与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一道被称为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之后的美国汉学“三杰”。史景迁,1936年出生于英国,毕业于剑桥大学,1959年来到美国耶鲁大学学习,师从芮玛丽(Mary C. Wright)、房兆楹。1965年,博士毕业论文《曹寅与康熙皇帝》荣获珀特尔论文奖(The John Addison Porter Prize),同年留校任教。 孔飞力 代表作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魏斐德 代表作《中华帝国的衰落》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史景迁出版十余部有关中国明清及近现代历史的叙事作品,他的作品特点是雅俗共赏,在学术作品与通俗阅读之间把握着微妙的平衡。以优美晓畅的文笔、严谨的历史考证,将中国错综复杂的人物与史事,用“讲故事”的传统历史方法,娓娓道来。史学家许倬云就曾这么形容过史景迁高超的叙事能力:给他一本电话簿,他可以从第一页的人名开始编故事,编到最后一个人。大众层面的畅销和学界的诸多质疑,大都源于他独树一帜的历史叙事风格。说故事,还是写历史?在很多批评者眼中史景迁不是一个“合格”的历史学者,钱钟书甚至戏称他为“失败的小说家”。 但面对诸多争议,史景迁似乎从未放弃一以贯之的治史方式和表达策略。在“叙事的复兴”(The revival of narrative)的大气候中,他以丰富的史料和多元的历史想象为砖为瓦,搭建起一座他的叙事王国,并把各式各样的人物召唤进来,有帝王将相,有仕人大夫,也有平民百姓,诉说他们的喜怒哀乐。他的叙事王国中,显而易见的是、史料、想象,不易察觉的则是为弥合历史理论与历史书写缝隙而作出的某种努力。 “讲故事的人” 与 “叙事的复兴” 学者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人类简史》(Sapiens: A Brief History of Humankind,2012)中提出过一个有趣的观点,他认为人类的祖先智人之所以能在诸多族群中脱颖而出并延续种族,根源在于智人语言的独特功能:讨论虚构的事物。这种“讲故事”变成了一种核心技能,它可以让人类集结起来,建立一整套合作机制,使人类族群站上食物链最顶端,成为地球的霸主。 赫拉利 《人类简史》 虚构不存在的事物同记录已发生的事情成为人类组建社群的基础,“讲故事的人”慢慢成为组织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叙事”可能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叙述故事”也成为中西传统历史编纂的基本体例,无论孔子、司马迁还是希罗多德(Herodotus)、修昔底德(Thucydides)叙述的历史都是去芜存菁,运用明畅的文字语言讲述一个个动听的故事。 希罗多德 代表作《历史》 修昔底德 代表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新史学”逐渐成为西方史学主流。以“叙事”为主的历史编纂体例受到了严重挑战。以法国年鉴派为代表的“新史学”认为,历史不应讲述故事,而应该是“分析式”的。不得不说,分析体的历史书写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历史研究的范畴,内容丰富的社会史研究逐步取代了传统的政治史研究的主流地位。而形式上,以“问题”为导向的观念也使得“分析”取代了“描述”。然而,分析就必须遵循科学的规范和程序。似乎原本“讲故事的人”对故事已然失去了兴趣。写作形式的程式化大大削弱了史学原有的故事性和可读性,史学作品离公众的通俗阅读越来越远。 直到70年代,“讲故事的人”才被慢慢唤醒。新一代的年鉴学派纷纷逃离“分析模式”的写作,重新转向“叙事”。代表作品如,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蒙塔尤》(Montaillou,1975),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的《奶酪与蠕虫》(The Cheese and the Worms,1976),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的《马丁·盖尔归来》( 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1982),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屠猫记》(Great Cat Massacre,1985)等。这类作品具有明显的叙事特征,既不是对传统叙事的简单回归,也不是与“新史学”的彻底决裂。在研究的主题和方法上,他们继承了新史学的积极成果,写作形式上也是叙事与分析并重;与传统历史叙事一样,他们都是关注人物,但研究对象往往是被主流历史遗忘的平民百姓,小心翼翼探寻他们的潜意识领域,探寻特定行为背后的文化心理因素。这群作者也常常被冠以“新文化史”或“微观史学”研究者之名。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 代表作《马丁·盖尔归来》 电影《马丁·盖尔归来》海报 娜塔莉作为编剧顾问参与该片制作 通过进一步研究创作了同名著作 史景迁成名于70年代,刚好处在“叙事复兴”的史学思潮之中。虽然在可见的访谈或自述里,史景迁没有直接提到“叙事复兴”带给他的具体影响,但仔细分析他的作品,依然可见两者的共同点,同样关注个体生命,重视细节的作用,着力发掘新史料,十分注重“深度描述”等等。史学家不可能脱离所处的时代和文化圈层而独立存在,史景迁似乎把这种影响内化作属于自己的一种表达方式,与“叙事复兴”有联系,却又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 大写的“人” 史景迁的叙事王国里,最有魅力的当属各色各样的人物。写人是他历史叙事的核心主题,如史景迁自己所言“我发现,只有当我将历史题材与某个与之直接相关的特别的个体经验联系在一起时,我才能真正把握这一题材。”无论何种身份、何种地位的人物,史景迁都平等地将他们视为历史长河中曾经生活过的一些人,诉说这些人如何以自身的禀赋在所处时代和环境中生活与思索,发现存在的意义,实现生命的价值。在史景迁的笔下,这些人物的血与肉才真正丰满起来,成为了大写的“人”。 史景迁主要作品中的人物 总体来看,他的著作时间跨度大、人物类型丰富,几乎涉及到晚明至近现代中国的多个阶层、多种视角。有平民阶层的王氏,有知识分子张岱、曾静、丁玲、鲁迅,有教士阶层胡若望、利玛窦,也有帝王将相如康熙、雍正、洪秀全。这些人物的共同特点在于都面临两种文化的碰撞,或是新旧之间,或是中西之间,面对相似的困境,个体生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描写类型丰富的人物,一方面代表史景迁治史范围之广,思考的维度可以跨越几个世纪,并从容驾驭多个时期、种类驳杂的史料,灵活运用于历史叙事写作之中。另一方面表明,他既重视人物的精神价值,又考虑到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影响,在传统叙事史学与微观史研究之间打开了一条通路。 史景迁 探讨史景迁的人物写作,需要打破作品之间的界限,统观所有的人物以及人物之间构成的关系。通览史景迁的整个作品序列,不难发现他的人物写作可分为三种构型:个体人物、二元关系和群像视角。 个体人物,并非面面俱到的个人传记,作者大都围绕一个主题,突出人物的某一精神侧面,柔声轻诉人物与时代的特殊关系。《王氏之死》中,记叙的是残酷的大时代下悲剧的小人物,作者用四分之三的篇幅铺陈故事的背景——17世纪山东郯城的地震、饥荒、土地争夺、乡权冲突以及贞妇烈女的事迹,直到最后两章,王氏才出现,又迅速死去。篇幅不大的章节中,王氏的困苦、欲望和梦想被完整呈现,“王氏之梦”的段落也将叙事推向最高潮。王氏仅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作者期望表达的是更多孤苦无告的卑微平民,在天灾人祸中,如何保有自己尘土中生出的自尊与梦想。 《王氏之死》 不同于王氏的平民阶级,《前朝梦忆》中知识分子阶层的张岱同样面临自己的困境。张岱长久以来以被贴上“小品文作家”标签,经由现代文人如周作人、黄裳等反复强调和经营,几乎遮蔽了这位处于动荡时代且内心敏感丰富的知识分子。史景迁擅于从生活细节进入历史场景,他起笔于张岱活色生香的青年时代,美婢娈童、梨园吹鼓、华灯精舍、美食烟火、鲜衣骏马、古董花鸟,而这一切的繁华生活的背后隐匿的是一个即将倾颓的国家和与之而来的更大的精神荒败。这里更有意蕴的是史景迁站在张岱——这位史家的背后来看时代变迁。明清易代,山河破碎,斯文沦丧,张岱重回龙山,一边叙写史书《石匮书》,一边写作散文集《陶庵梦忆》,一重一轻都在释放张岱关于家族和时代的记忆。个体人物的写作构型,从本质上看,是史景迁饱含人文情怀的对于个人与时代关系的探索。 《前朝梦忆》张岱小像 二元关系也是史景迁观察人物的一种角度。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处理二元关系时,并不是平均用墨,而是意在将性格、地位、价值观迥异的双方放置于同一时空、同一事件之中,让这种关系自然呈现出一种叙事的张力。《曹寅与康熙》便是这么一对二元关系,曹寅“包衣”的身份让他娴熟地游走于满汉不同的文化圈层,如书中所写“在曹寅身上,满汉文化达到一种平衡状态。显然曹寅热切投入满族军旅那种豪迈的骑射生活,但他同时也是个对汉文化易感的诠释者。”他既是官僚,是天子近臣,又是江南汉族文人团体的领袖。曹寅复杂的身份给予作者更多的叙事空间,特别是同康熙关系的处理上。两人何以达到“隐密而微妙的交流,有时甚至不失亲昵”,曹寅并非康熙的肱骨之臣,仅是帝王的家奴,却能得到封疆大吏都没有的信任。曹寅与康熙这对二元关系背后展现的是更大的权利秩序,曹寅作为康熙私人密探的身份被一一剖析出来,同时,满清高度集权的统治手段也更为明了地被剥示出来。类似的结构还有胡若望与傅圣泽、雍正与曾静,史景迁的叙事,从一组二元关系论著一个时代,从细微之处直指历史的大方向。 《曹寅与康熙》 如果说个体人物、二元关系是微观的自内向外的叙事,那么群像视角则更能宏观地展现时代图景,叙事中人物与时代的关联性也会被进一步放大。《大汗之国》中,作者使用“观测”(sighting)一词,似乎能够诠释群像视角的某种特质,即“观察者藉观看预期的目的地而发现自己”。这里需要明确的是“观测者”与“被观测者”的问题。《天安门》的群体视角比较清晰,叙事层次鲜明,随着史景迁这位观测者的视角,来观测康有为、鲁迅、丁玲这三位主叙人物,以及秋瑾、沈从文、瞿秋白等辅线人物,即以西方史学家的眼光看待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面对国家兴衰存亡时的抉择。《改变中国》和《大汗之国》的“观测”体系则略显复杂。《改变中国》描写的是1620年代到1950年代之间,十六位在华工作的西方顾问,《大汗之国》则呈现的是自1253年到1985年间,四十八位身份各异的西方人对于中国的观察。在这两本书的“观测”体系中,第一层是西人看当时的中国,而第二层则是史景迁看这些西人。有意思的是,当一个中国人拿到这两本书时,观测似乎又多了一层,透过以上的双重观测来审视自己。当然这种“观测”也散见于另外两种构型的著作中,如《利玛窦的记忆宫殿》和《太平天国》。学者乐黛云曾说,用一种文化去解读另一种文化时很容易有“误解”,“误解”不一定符合被看一方的本来面目,但能开拓人的思想。如她所言,“史景迁的主要贡献是,启发不同文化要互看。”通过“观测”,每一种文化都能认识到“他者”的存在,而史景迁的群像视角,都是对作为“他者”的中国的一次追寻。 《大汗之国》 史料为砖 想象为瓦 历史叙事写作中,不可避免的需要面对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对待历史的“真实”与“想象”,客观史料与史家主观想象之间到底有多大的空间可以支撑起叙事性写作。兰克学派认为,史学家应尽量避免主观影响,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利用已有的科学技术手段,以纯客观的态度考订、辨伪史料,确认历史中发生的各种历史事实。这种观点长期占据历史学的主流,直到后现代思潮波及史学,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后现代史家对此提出了根本性质疑,“语言的不透明性使史料既无法完全呈现著述者的意图,也无法将史料自身完整地传达给使用它的史学家”,后现代理论意在消弭历史的“真实”与“想象”,似乎在史学与文学之间划上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约等号。 利奥波德·冯·兰克(左) (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 海登·怀特(右) (Hayden White,1928—2018) 而史景迁的叙事中,史料与想象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它们如同砖瓦,共同构筑起这片属于历史叙事的王国,作者自觉地将文学手法融入历史写作,给历史情节还原出更为广阔的时代语境。在他的作品中不难发现,史景迁非常重视史料的作用。《曹寅与康熙》中,作者以审慎的态度对曹寅的身世进行考据,参考文献达122条之多,但凡是假设和推断也都明白的指出,留待读者判断。对新史料的挖掘也是史景迁作品的一个特点。《太平天国》的写作得益于大英图书馆发现的两种太平天国文书;《王氏之死》来源于黄六鸿所著《福惠之书》中的一个案件;《胡若望的疑问》发端于欧洲发掘出的教父傅圣泽的三份抄本档案。史景迁同样将虚构类文学材料灵活运用于叙事书写之中。在他首部作品《曹寅与康熙》的部分章节,实际已经将《红楼梦》纳入史料的探讨范围;《王氏之死》之中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已经深度参与叙事;《天安门》中引述鲁迅等人的文学作品体现了“以诗证史”、“诗史互证”的理念。史料运用的广博和扎实,一方面为史景迁的历史叙事提供了坚实的事实基础,也为其想象力的发挥提供了诸多支点。 《王氏之死》中运用的三种史料 《聊斋志异》《郯城县志》《福惠全书》 想象同样是史景迁叙事王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柯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中认为历史想象力是“结构性”的而非“装饰性”的,即历史系统的“构造”本身是通过“想象”来完成的。当史景迁以史料搭建起一条并不完整的叙事链时,为了完型整个故事,想象力便开始发挥作用。《王氏之死》中“王氏之梦”,史景迁运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将想象力发挥到极致,描绘了在极尽绚烂的幻境中,王氏如何一步步走向死亡。作者在《胡若望的疑问》结尾,虚构了胡若望返乡后与家乡孩童的对话,将叙事引向了欧洲之旅,与“启程”章形成前后呼应。史景迁的历史的想象带来一种副产品——文学性的氛围,他的历史写作总是与文学作品产生一定的互文性。《曹寅与康熙》同《红楼梦》一实一虚,描绘出一个封建大家族的罗曼蒂克消亡史;《王氏之死》与《聊斋志异》一真一幻,残酷的现实同美丽的幻想形成的巨大反差,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叙事张力;《大汗之国》的最后一章,以卡夫卡的《中国长城》、博尔赫斯的《曲径分岔的花园》与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为研究对象,论述、叙事游走在史料与文学之间。再如《康熙自画像》以第一人称的自述视角,展示多重身份的康熙作为帝王、父亲和文人的复杂内心;《胡若望的疑问》运用日记体例加“上帝视角”,来探究一个生如草芥的平庸小人物如何被记载入世界三大资料库中。 卡夫卡《中国长城》 卡尔维诺(左)与博尔赫斯(右) 胡适曾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词》中谈到历史学家应具备的两种能力:精密的功力和高远的想象。“没有精密的功力不能做索求和评判史料的工夫;没有高远的想象力,不能构造历史系统”。史景迁的作品很好的平衡了史料与想象的关系,他在创作中有意识的将“文学”(literature)与“虚构”(fiction)区分,“文学表达出的是一种品质,一种判断,或是某种处理语言的方式方法。”想象的虚构、史料的活用是技巧,达成历史叙事的文学性才是他作品的要义。 “匿名”的理论 在史景迁的叙事王国里,可见的是形形色色的人物,是丰富多元的史料,是富有文学性的想象,但不那么显而易见的,是他为弥合历史理论同写作实践之间的缝隙而做的某种努力。“我对把理论在写作中横加插入的做法没有兴趣”,史景迁的叙事写作有意识的与各路理论、流派、风潮保持距离。历史叙事的多元性很难让人把他的作品框定在某一种理论架构中,这也成为他的作品被诟病的一个原因,“缺乏创新的观点”“没有分析”“不能解释问题”常常是评论者对他作品的负面看法,这些论点都是从历史写作是否符合学术规范的角度出发,然而,所谓学术论著式的写作并非史家写史的唯一表达方式。 史景迁的处境与杜尚(Marcel Duchamp)在20世纪初的艺术界的状况颇有几分相似。杜尚以艺术的自觉,刻意与达达、超现实主义等保持距离,对流派间的党同伐异嗤之以鼻。1917年,美国“独立艺术家展览”上他的作品《泉》突破艺术理论的桎梏,打破了生活与艺术的界限,反叛地放弃艺术的感性美,转而服务于思想,打开了当代艺术的大门,其先锋的理念也影响至今。 杜尚《泉》 同样,史景迁的写作少有理论先行或概念先行,他化理论于无形,深刻地融入到叙事之中,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把理论以“匿名地(anonymously)”方式放入写作之中。在与学者卢汉超的对谈里,史景迁表示,“对理论的一种过度的强调其实是有局限性的”,“大部分社会科学理论都是相当短暂和过渡性的”,“如果我对某个理论有兴趣,我会用一种称之为匿名的方法采用在我的书里”,“当我认为某种理论有价值时,我只是用它来影响我叙事的方法”。与杜尚不同的是,当代美国史学界似乎比20世纪初的艺术圈宽容得多,不但在2004-2005年度当选美国历史学会主席,还以其“叙事性历史写作”获得数额巨大的麦克阿瑟基金会奖金,得到普遍认可。 史景迁著作中译本 “叙事复兴”的大背景下,人物、史料与想象构建起史景迁的叙事王国,写作实践中作者将理论化于无形,实现自己的史学理想。史景迁通过历史的叙事写作,以人文情怀关注历史中鲜活的生命个体,展现不同时代下人们的精神状态。正如余英时先生在《天安门》的繁体中文版序言中写道:“从正面或侧面勾勒出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这是史学家的真本领,也是史学的最后归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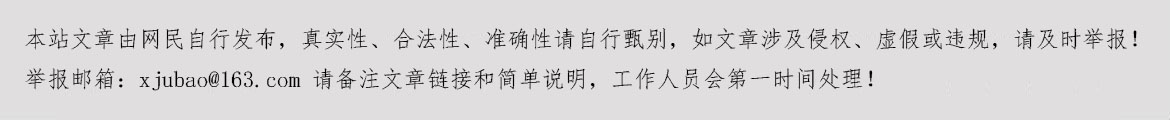
|